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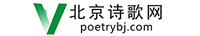

白色的房子(正式稿)
19701113 2023-02-13 11:20:01
白色的房子
李红丰
我一看见它、想起它、梦见它就恶心,但又不得不面对它,你说该怎么办?你似乎有好的办法,能告诉我吗?
一
昔日的他是一个默不作声的少年,神情忧郁,但有时候非常倔强,瘦削的脸容跟梦想者相类似。他说:“他时常梦见他的同学们突然消失。不幸的事,是他无法消失”。你能相信他这种说法吗?我好像不能相信,你呢。
他说:“十多年前,他正在一个小城里读书,那地方非常偏僻,一到夜色降临时,就不时有绿油油的磷火在四处不停的闪烁,就好像这个城市每逢重大的节日里都要燃放的礼花一样,以示庆祝所谓特定人群的胜利。它的样子十分好看,而且常常令这世上的人沉醉于其中。那里的建筑也非常奇异,你不管左看右看,还是前看后看都是一样的,是个四方体,就跟火柴盒似的”。
他的颜色跟他的经历相仿,外表红黄红黄的,就跟染上重病需要放出的血一样的,令人沉闷、徘徊。住在里面的人,好像全都有洁癖,他们总喜欢把这内部刷得白白的,似乎不愿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这想要证明什么…………
我想,他们的目的恐怕是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贞节的女人吧。这发白的颜色就跟这屋子的人裹尸体所用的白布相同。它的走道回环往复,就跟迷宫似的,常常令人头昏脑胀。
他说“在那个空间,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他常常搞错所有的东西,更要命的是他常常分不清楚白天与黑夜,但却总认为白天与黑夜是一样的”。
他说“到了后来,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在这个虚无的维度里,留下自己不朽的痕迹,那怕它只是一道淡淡的血痕。”
他又说“痛苦对他来说,就像每天必须要喝的水一样,已成为他生命中的常态”。
二
一些奇怪的建筑在场地中央矗立着,颜色是红红的那种。远远看上去,它的分布似乎始终笼罩着一种梦幻般的状态。但你如果决定走进去,在里面看一看。深处其中的人常常会用那整齐划一,精密安排的言辞来驳斥我,他们神态庄重严肃,用语尖锐犀利。对此,我或许无法抵挡、也无法回答,可能他们的确代表那所谓的“唯一”。我想,就让他们代表去吧。
他们觉得这奇妙的建筑里面有着一种精妙的合谐,不但因为这合谐来自远古的梦幻,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在某种杂交状态下的完美统一。我想,就算它也许看上去是一种杂乱的状态,或者说是呈现出一种四处混交后,零乱的样子。但我所无法否认的,这是住在里面的人最喜欢的一种时态。它的颜色非常奇妙,是红红的那种。
这可真是个特别的地方。这里的季节与众不同,尽管在这里也在进行同样的四季变幻,但它好像已拥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季节。天空的云彩虽然也跟别处一样在进行不停的组合、变幻,看起来也多姿多彩的,但它在慢慢的收缩,收缩于一个难以平衡的支点。这儿时间也怪怪的,虽然它也像其它地方的流水那样在慢慢的流逝,但它似乎更在走向停滞,停滞于某种难以说明的空隙。
“你看清楚了吗”?“你看清楚了吗?”
一个莫名奇妙的声音在这不大的空间回荡着,就像一个已消失久远的幽灵。不知何时,我已站立在这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在呆呆的望着这变幻莫测的天空。厚厚的嘴唇在不停的嚅动着,像是想要回答这幽灵一样的声音,不知怎么搞的,可这嘴像是不听使唤,不管我怎么努力它都不愿发出声音来,此时脸上的肌肉也更着抽动起来,在不停的努力着,可就是怎么也无法说出那人人都应听得见的声音来。慢慢的,我就一直这么努力着、尝试着……
我真的想拥有这种说话的权利。我是一个沉默无言的人,也是一个陌生感极强的人。我非常害羞,似乎这一辈子都无法面对在我面前发生的任何的事情。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天空中有一种声音在慢慢的回应道,它像是经历了漫长、艰难的岁月才走到这儿来。这声音浩渺悠远,是一种久经沧桑的声音。我茫然无措的站着。我像是有了一种思絮。我想,我现在已能维持这行走的平衡,已拥有能在这不大的空地里不停打转的能力。我慢慢的向前走着。可远远看上去,我更像在用那茫然的眼神不停的张望这狭窄的天空。
我在不停的在寻找着……但我在寻找什么?我也不知道,谁能告诉我。
时间在轻轻的流过,不知何时,这额头上的虚汗已经冒了出来,这发烫的虚汗有点特别,看上去它似乎与其它普通的汗水有着很大的不同。我想,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银白色的如雾松般的晶体。真的,它时常会在金色阳光下不停发射出那耀眼的光芒。它在不停的向外蒸发,也像是在酝酿某种力量。它非常努力的在做。此时,苍白的面色已经红润了,就像某种神秘之手在素白的尸布上不停的涂上了那一层一层薄薄的胭脂。我呆呆的站着,似乎怎么也无法发现这声音的来源。
“它到底在那里”?真的,我感觉它似乎像是在自言自语。
“不对,我好像看错了”。
“它的颜色似乎跟染上重病的人必须要放出的血一样,红黄红黄的”。
“真的,我觉得它是让人挺恶心那种”。我喃喃的抽动着嘴唇,似乎是在努力想要把这口水似的话说出来,可惜,我失败了。
“对不起,哦!我想起了,它好像是某种时代的颜色,对不对?”。嘴唇喃喃的抽动着,但仍然无法发出他应有的声音。
“抬一下头吧,你的面前好像有一个小虫子在一个不停扩展的蜘蛛网里挣扎吧。”
“对的”。我只能垂下我的头颅惯性点了一下。我心里在想,真的,它好像是某个不太遥远时代的基调吧。
“你在仔细地看一下,那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的人群都穿着这种颜色”。这好像是一种维持生存的颜色,是一种保护色。对了,那里好像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烟筒,它特别喜欢冒一种紫色的烟雾。风在轻轻的飘着,慢慢的它停滞在某一个难以确定的点上。
哦!它的确是一种挺神秘的颜色,似乎还具有那神鬼难测的轨迹。我在心里默默的想道。它真的就像图腾一样,奇异、鬼怪。是的,我无法否认它天生就具有让人崇拜、屈膝的那种味道。
这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四处长满了杂草。我想,你如果想行走于其间,冷不防会在杂草丛生的场地里踢上那怪模怪样的砖和残缺不全的瓦片,这怪模怪样的砖准会使你的脚丫子痛上半天。这砖看上去颇为怪诞,挺像某种时代的艺术品,现在看起来,它似乎更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想法。你觉得奇怪吗?是的,的确有的奇怪。此时,我的心似乎在不停的冲击那早已死亡的眼神,它就像那风化的石片一样在一片一片的被剥落。
三
天已进入了黄昏,原本蓝蓝的云彩也渐渐的消失了,取而代之更像是一种玫瑰红的颜色。不知怎么搞的,这个季节平时难得一见的雾也慢慢的笼罩下来,一圈一圈的就像某种炊烟似,给人的感觉就像生锈的铁屑被风吹起在天空里四处飞舞。
他说“他的眼里常常出现某种幻觉,他的生命历程就像无法摆脱的恶梦似的”。语调突然停顿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此时他已呆呆的站着,把双手伸向了天空,像是在积聚某种力量。
不一会,他喃喃自语道:“那时的他常在四方形的盒子里生存,就像盛放死尸的棺材的浓缩版,它只不过比棺材的尺寸时而大一点,时而小一点而已。四方形的盒子里面常常变幻着两种色泽:一种是涂着黑色的漆,它的光亮无比就像华发凋零后的夜晚;另一种就像少女那失血已久,怎么也无法掩盖的那苍白的面容,不过它常使人想起白雪纷飞的颜色。”
“我想里面的主人也许会觉得这样的颜色组合过于寒冷,也许明白这样的变幻这么也无法奏响那响彻云霄弦律。所以他们试着在它的外表面涂着某种在国人看来是一种喜气的颜色,这种颜色似乎与胭脂的颜色相仿佛,红红的。是一种脂粉流出的颜色。”他的家乡在这条河流的中下流的一个小城里,小城的旁边有连绵起伏的山川,小城在山的底下,是挺秀丽的那一种。
他是好久来的,我不能肯定的,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好像是一路爬起来的,像是一个人似的,挺直了腰,不像是缺钙那种。当然,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昏沉沉的、血肉模糊地一直向前爬,他爬近了他的目的地吗?我也不知道。
神情恍惚的我,在慢慢的向前走着,就像一个幽灵似的在四处飘浮。没有走多远,一座仿佛在某种外力的情况下修建的建筑就挡在我的前面.。拦住了我前行的去路,飘浮的眼睛向前面看了一下,很快就闭上了。我呆呆的站着,嘴唇在不停的抽动着。不知怎么搞的,我觉得自己像是走错了地方,我好像来到殡仪馆存放骨灰的房间,是吗?我心里在不停打着鼓,双腿忍不住颤抖起来,已无法维持这站立的平衡,似乎很快就倒下。
这幽灵的声音像是已看穿了我的心思,轻轻的用他沧桑的语调在这不大的天空中说道:
“我想,你不会胡说,不会的。的确,这里的确有着一种特殊的味道,特殊的气氛”。那沧桑的声音就如同那断线的琴弦在划破这不大的天空。
我心里在想,我是不会搞错的。但这种说法你相信吗?
不相信,是的,我也不愿意相信。但事实会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能告诉我吗?
我只知道,这些叙述应该是事实吧,不然,这还算比较大的长方体怎么会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矩形体,大小正合适。因此不管你怎么看,是从左边看、还是从右边看;从上面看、还是从下面看;从正面看、还是从后面看,看起来似乎都跟骨灰盒相仿。
此时的我似乎已能在地面上站稳,颤抖的双腿似乎也停止了那不停的颤动。不知过了多久。我像是已拥有了某种勇气,一种令我能说出话的勇气。嚅嚅的嘴唇在不停的努力发出那在别人看来是十分正常的声音。慢慢的,它似乎发出声来了,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在这不大的天空里回荡,这奇怪的音符听起来似乎怎么努力也无法连成一个完整的词语。我非常奇怪,这时的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这样的奇迹的发生,真的,我不知道我在何时拥有了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胆量。不过这声音听上去已没有丝毫胆怯而迟疑。我正常了,是真的吗?微风在轻轻的吹着,似乎已走出了这野草丛生的沼泽地。
“你-还-敢-往-前-走-吗?还-能-一-直-往-前-走-吗?”
我想“如果能的话,那么你和我的灵魂就会像两颗奇怪的幽灵在这儿飘浮,但他们能消融在一起吗?”
“算了吧,还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吧”。断弦的声音轻轻的飘了过去。
“它好像是被人为修复成这个样子吧,是不是,你能告诉我吗”?
“你不是好称具有博古通今的知识、沉思独立的人格吗?”
你沉默着,就如同那一片飘逝的树叶。风不知何时停了下来,这空间似乎也跟着沉闷下来,像是得了某种慢性病,懒懒的就如同昏睡已久的病人。
“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我想,“这问题对你来说应该不能回避吧”。
“以前的这个建筑是个什么样子”,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它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它的本来面目会是怎样的”,
“最初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修建”,
“他们是怎么考虑这地下的基础”,
“你想到没有”,
“如果不搞清楚它”,
“我们怎能修复成它在这个世界上‘应该的样子’”。
我几乎不停的在说道。我似乎已拥有了某种自信,更像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我能说话、我能大声说话、我能表述自己意见的权利。我兴奋了,那苍白的面容此时已冲满了那带有血色的红晕。
我似乎在一直不停的唠唠叨叨。我想我现在是在某个空际无人的地方,在发表那看似神授的演说,或者是在说着那种看是已经枯萎的内心的神秘独白吧。我像似是在揭露着什么,我似乎已知道了某种秘密。
我想是在追问什么?我继续说道:
“在这一点上,我想你应该是知道,也应该明白的吧”。
“你只是想避开这个问题吧”,
“它是不是对你来说太敏感了”,
“尤其是对你的过去”,
“这会揭开了你的伤痕,是不是”?
我不停的说道,已全然不顾这四周是否还有回音,是否会听我这唠唠叨叨的话。真的,我只是不想放弃任何的机会,那怕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机会。我已经明白,我现在已拥有了可以思考的权利,已拥有了和所有的人平等对话的权利,不管我曾经是什么,将来是什么。现在,我已坚信这种权利是任何人、任何貌似神灵的东西都不可以剥夺的。风在轻轻的飘过,就如同这逝去的流水。
“你怎么沉默不语了”?
“你是在伤心、在流泪、在独自的哀叹吧”。
“你现在是不是还在一直沉默”。
四
我想,“我还是得往前走,可不能管它是个什么样子,不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能抛弃它、回避它,能一身轻松的向前走吗?”
“我想这样做,但是我能吗?”
“我想我不能”。
“那么,我只有自己尝试着来猜想、尝试着来解答?”
“有其它的办法吗?”
“但愿有吧。我渴望能找到它,但是去那里才能找到它”。
血肉模糊的他不解的问道:“难道非要找到它,它真的有这么重要,不要它行不行”。
我想,“不要它恐怕不行。一间房子总不是凭空建立起来,不管怎么样,修建房子的人总得要知道地下的基础,这一点上,你总无法回避吧”?
“你如何能何回避得了。试想,如果你对地下的基础都不了解,就在上面盖房子,难道你不怕它跨塌吗”?
“在这点上你能侥幸过关吗”?
“你相信你有这样的运气吗”?我是不相信我有这样的运气。
不过,这怪异的建筑有时候看起来似乎像一条龙,这可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它是某种民族长期生命顶礼膜拜的图腾;有时它看起来似乎更像一条猪尾巴,它似乎就好像是人头上长的那种;有时候看起来又似乎像一座堂皇的宫殿……
我想,“这两千多年来有不少的人似乎和你想法一样”,
“那就是试图避开它”,
“不去了解它的基础”,
“只按照模糊记忆中的样子重新去修复它”。
“不在去管它的基础是怎么样,应该是怎么样”。
“就这么混过去,实在不行就充其量在里面、外面修饰一下,以此来显示它的久远、它的博大精深”。
“时间一长,可就没有人敢去想它,敢去碰它”。
真的,“如果有些特别的那也好办,那就让他悄无声息的消失吧,就像这飘零的树叶一样无声无息的消失”。我的思絮就这么磕磕碰碰的,段段续续的,似乎就是从来都没有完整的说完一句话。我继续说道,此时,我似乎已不知道什么是疲劳的感觉。我像是已拥有了那无穷尽的力量,似乎是必须向外喷洒。
“其余的,那就更好办,就要让它烙印在他们的骨肉里、溶解在他们的血液里”。
“你怎么不回答,你沉默了,我的说法对吗”?它是不是触动了你的痛处。
“它就像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庙,是一座被烧毁的古庙吧。燃烧时,那火焰的颜色是红红的,与流向四处的鲜血是相仿佛的吧”。
“已成废墟的它,这四处断壁残垣的颜色是不是已流尽鲜血的苍白色,它是不是跟僵硬的死尸相仿佛”。
“里面所供奉的神似乎也被烧成乌黑乌黑的,是不是还有不少蜘蛛网悬挂在里面,你看见了吗?看清楚了吗”?
“是这样的吧。”
“它好像很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来朝拜、来屈膝磕头。”
“我的说法对吗?”
五
“这个外来的人清醒了吗?”
“他现在在那里?”
“他来到这台座下吧,他是不是躺在这里,这台座的下面。”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是在照射这片大地吧,我想是在照射吧;在照射这座建筑吧,我想它应该会吧。他发现了他身上的伤痕都已结了疤吧,是不是。我想他应该发现了。
他闭上了失血的眼睛,睡了过去,我想这并非他体力的衰弱,而是他的意志的问题。他是想好好的睡一觉吧。我想,他的确是应该好好的睡上一觉,只是不要睡死了,永远不在醒起来,就行。
“我在那里,是和他相遇了吧。”
“我想应该是如此。”
“我会躺在那里?”
“我能得到与他相同的经历吗?”
“这个问题重要吗?”
“有这种可能吗?”我不停的说道,像是已无法停止下来,水就这么一直流着,我似乎用尽的所有的思考都无法找到如何关闭、让它停止的办法。
“哎!水就让它这么流着,它已沉没了很久,你又何必去想办法关闭它。”
我想,这并非是一种浪费,而是一种上天赋予他的权利,一个生长在这段空间、这段时间的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它有它说话的自由、说话的权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但你不能剥夺他。你必须容忍它,因为这必定是宇宙的法则。
不知怎的一种不寒而傈的恐惧,一下子传遍了我的全身,骨髓中的神经不停的颤抖起来,飘浮不定的我不知是否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这地方上面有河流吗?”
“上面的河流会不会被枯死、被封死就像这布满山川的死尸的一样。”
“这地方除了他、久远的你、我还会有人来过吗?”
没有人来过,不会的,我想应该有人来过吧。不然,这许多赤脚的脚印、一些不知名散落在四周的果子,就是例证。对了,不要忘记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备的东西,何人能抗距,你能例外吗?我自言自语道。
“一只水罐都没有能存在……你想想这对你意味着什么,难道你没有想过”。“找到那些东西有能说明什么?”
沉默已久的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我兴奋地迎上前去,我以为我终于等到这一天,可是你却又像幽灵一样飘走了。不再开口就像沉默的树叶无声无息的消失在这死水里……
我失望极了,一不留神自己也就像飘浮的树叶一样落在了地上,不知怎的,还在地上打了几个圈。无奈之下,我只好不停地再向前飘。
这恼人的风不知为何要在此时刮起,真是令人伤心。眼我就要飘在了那供奉诸神的神龛里,这一刮,就把我吹在了这不知名的灌木丛里面。
六
他就是这么一路爬过来的,有可能吗?他是不是用了别的办法,你和我都不知道的一种途径。
“我和他为什么会在这儿相遇?”
“你能告诉我这个秘密吗?”
“你是不是早已无能为力?”
“你告诉我吧,为什么不再回答。”
“你是害怕了吧,不然你为什么要沉默。”
“你是不是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欺骗……而感到伤心绝望。如果不是,那么你为什么要把我引到这里来?”
“你为什么要使他昏沉沉的、血肉模糊地一直向前爬?为什么”?我似乎已能说一些稍为完整的话语,这独角的演说似乎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如果你这样长期沉默,那么你会失语的,你会害怕这种情况?”
“也许你不会在意这种情况的发生。”
“你的瞳孔会放大吗?”
“你的眸子会看见他睡梦中的一切吗?我想你会看见。”
“他会有梦想吧,他现在是不是在梦游,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地,你知道吗?”
“他是不是刚从粘糊糊的沙漠里钻出来,是在一个天空如血的时候出发的吧。那时,天空里全都是朦朦胧胧的光线。你难道不觉得这种时刻最容易搞错,我想我会常常搞错,总会把它误认为是灿烂的黎明,他也不会例外,你会例外吗?”
此时的我已成了一个隐居的哲人,已拥有了睿智的思维,似乎还拥有了演讲家那思辨如海的口才。我已是神授之子,只能接受那上天的的启示。
“我是一个罪人,一个有着弥天大罪的元凶。”
“真的,此时拥有一个真实的记忆似乎对我来说已成为一个成为圣者的障碍”。
“我得承认我是一个罪犯,有着这人性所有的贪心与欲望”……
“我承担着这世人所有的罪名”。
“我虚伪、自私心重而且还盲目自大,不知如何真正的反省,我只愿做那好看且功利性极强的表面文章”。
“这青春是腐蚀了,有如一具腐朽的尸体,瞧!这漫无边际的空气似乎已被我所渗透”。此时我似乎已成为了这空间与时间的主宰。
我在这黑暗的房子里躺着,感觉到自己好像已经失去了对岁月的记忆。在某个时候,我是不是曾经年轻过。那时的我好像还能做梦,还能在空间里移动。现在,我在干什么?有没有别的办法走出去,好像没有别的办法,我好像只能以现在的姿势等待某种安排,是不是命运的安排。我也不知道。
七
一道飘乎的闪电正飞快的掠过这蓝蓝的天空。霎时,袅袅的青烟已经升起。这苦泣的瞬间里,一个生命的极限似乎已被击穿。亮丽多姿的云彩似乎也如同这四处飞溅的黑絮在飞快的裂解、飘散……
此时,黑色的雾、黑色的絮似乎成了某种时空、某种生命的主宰。那飞流直下的痕迹就如同那从融化的冰山里流下的奔腾不息的雪水在山谷里不停的回荡、盘旋……
我知道,生命只不过是某种令人眩目的幻觉而已。很脏,五颜六色垃圾和泥土常常飘浮在上面,就像给人穿上的衣服一样,五彩缤纷的。屋外的小溪在静悄悄的流过。不可否认的是,有时它会呈现出某种海市蜃楼般的幻影,时常还被诚信的人们认为是某处的佛光在某个恰当时候的出现。
八
腐尸的味道已在慢慢的扩散。不大的天空里,变幻不停的云彩似乎也在慢慢的消失。慢慢的,它似乎成了某种主宰,就像这无所不在的空气一样。
晨曦也在慢慢的蜕变。令人眩目的光线也在慢慢的萎缩,它似乎也跟某种东西一样被腐蚀了,似乎它也无法抗拒这演进的速度。
“你也在渐渐的萎缩吧,萎缩成一块躲进地表的化石”。
我知道,“这长期冬眠的化石几百年、上千年后就会在某个恰当的时候出土,那时的人们就会像现在的人们一样对这早已逝去的东西进行顶礼膜拜,把它当成生命中的上帝”。
“某种味道的干尸已被出土。不同的,它是具保存完好不曾风化的干尸”。
我只是想知道,“这具出土的干尸里是否还有鲜血流过的痕迹,是否还有水的蒸气”。
“真的,我不知道,你能告诉我吗”?但我知道的,“已入空气的它将会有那神秘莫测的露水”。
你曾经说过,“那时的你曾像那干渴的行人一样渴望四处都有你那呐喊的回声”。
“可是这沙漠中的人生让你失望了吧”。
那时的你还说:“你那重重叠叠的一生中所看到的都是海市蜃楼般的幻影”。
“可惜的是,年少的你常把它当作理想与梦想的光芒”。
你又说:“那光彩夺目的幻影曾是你生命中的全部”。
“那时的你常常散发一种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蒸气”。我知道,“它是你血液奔腾不息的温度”。
“那时的你渴望理想与梦想的实现”。
“你难道,真的愿意所谓的宿命就是那尘土飞扬中的泪珠在空气里不停的晃荡”。
“你真的期待琥珀的眼泪融化你那奔腾不息的生命”。
“我真的不明白,但如果你还要沉默,那就独自去沉默吧。”
“不管怎样,我还得往前走。”
“你还往前走吗?”
“我能等待到你我再次相遇的这一天吗?”
九
涂满白色、光线黯黯的走道,回环往复、狭窄的空间就像某种四方形的组件。这似乎是人们根据某种需要进行组合的。不知何时,冷冷的月亮就悬挂在这略显孤独的天空上。天空暗暗的,就像深蓝色的幄幕与黑色的战车在金色的太阳与红色的鲜血搅拌下的融合体。
在黑色如漆的元素下,只有几个孤零零的树投射出那笔直如剑的枝干,枝干上已所余不多的叶子在瑟瑟的风中颤动不已,附近不远的地方似乎有着某种孤零零的火焰在燃烧,风在不停的刮着,这飘浮不定火焰的颜色时而绿幽幽的,时而像鲜血一样的红。
慢慢的,寒冰似铁一样的光线就如同这无孔不入的水银铺满了整个大地,风也在慢慢的吹着,整个空间似乎像得了某种慢性病似的,懒懒的,以近乎死寂一样的空气在慢慢的流动着。
一个飘浮的影子出现了,步履踉踉跄跄的向前走着,不知怎的,在一座奇怪的建筑面前停了下来,他犹犹豫豫了半天,似乎还是迈不开脚步。远远往去这似乎是个年轻,还未成年的学生,一脸的忧郁,跟某种梦想者相类似。他身材不高,略显方形的脸和呆呆的眼神常让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以及所有的人认为他是个白痴,说句比较好听的话就用这些人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智力尚未发育全,天生就是一个白痴。他似乎常常闹笑话,他们说他最大的毛病是在课堂上经常用前言不达后语的词句回答在旁人看来十分简单的提问。
他的同学曾说道:“这些问题,他们可以不加思索就能回答”。是的,他常常提出他们看来是常识的问题。
是的,他的智力的确有问题,而且从不否认,他认为他的确是个白痴。
他慢慢朝前走着,犹犹豫豫的。他低着头,两只手时而不停的搓着、时而不停的晃来晃去,似乎这不大的空间里没有容纳这双手的地方。时间向前慢慢的流逝,过了一会,他才局促不安地墩在地上,看着地下,似乎这地下面有着让他自在、不在难受的东西。
我知道他像一个受惊的小鸟一样,害怕世人的走近。他孤独、脆弱,有着一颗敏感的心,但他似乎怎么去努力做也不能回避这些让他难受的东西。他就这么一直墩着……
天似乎也快亮了,这时间似乎跟他过不去也就这么就一直停滞下来。周围一片寂静。不知怎的,一种腐烂的味道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慢慢的充塞这不大的空间,空气似乎也在慢慢的变质。不远处,几支孤零零的树在静悄悄的站着,风似乎也停了下来,似乎它也跟着时间一起消失了。
这座奇异的建筑似乎没有关灯的习惯,或许它是想让这座建筑永远没有黑暗,让居住在里面的他们始终处在阳光般的温暧。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
天似乎已经亮了,微微的光似乎在照射着这不大的空间。不一会,三三两两的人从这座建筑物里面走了出来,他们的脸色体现出一种勤劳后的亢奋,整夜未眠的他们似乎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似乎出席了某种盛大的筵会,他们的言谈显示了某种刺激下的满足感。
布满血丝的眼框、充着血的眼球、红嘟嘟的嘴唇似乎像喝了许多血似的。我或许看错了,也许他们整夜都在喝一种跟血液相仿佛的葡萄酒,吃着跟动物尸体一样的面包。他们的手红彤彤的,犹如艳丽的桃花在圣洁的天空下绽放。
在水银似的光线照射下,这每双手似乎都像涂满了胭脂、都像涂上了红色的墨水。他们似乎是刚从战场下来还未来得急清洗自己的双手。他们的衣服鲜明光亮。他们昂首阔步好似时代的骄子。
这座建筑物的里里外外种满了葵花,但他们似乎不约而同的只栽一种,一种朝着太阳、迎着朝霞的向日葵。天似乎更亮了,红彤彤的一轮朝阳似乎也在慢慢的从海平面升上来,金黄色的光芒似乎也是从那儿在慢慢的散发出来。天空似乎也在慢慢的变红。
畏畏缩缩的他一直还墩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他的双手近乎僵直,他似乎没有感觉到光线的存在,他想是睡着了,他看上去非常疲倦。金黄色的阳光已经非常明亮了。此时,这奇奇怪怪的建筑、这里里外外的向日葵似乎像是从某种沉睡中苏醒,它们像是在拚命的吸附着什么,就如同人造海棉那样不停的吸附某种肮脏的东西,它们自身的力量已经枯竭,已无法维持自身赖以生存的平衡。
太阳升得越来越高,金黄色的光线也越来越强,慢慢的似乎每个角落都被它照射着。他还一直在那里墩着,似乎这十分强烈的光线跟他没有关系。他的周围似乎也没有这金黄色的光线,似乎这能量在他身上已不复存在了。
他就像一座冰封已久的雪山,我不知道。我想,就算是冰封千年的雪山它也无法抗拒这金黄色的光线。难道他是一座冰存于大海下的雪山,我想也许是吧。
慢慢的,这奇奇怪怪的建筑不停的向外发射出那金黄色的光芒。刹那间,它光芒万丈的铺照着整个大地,似乎更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
是呀!一个人造的太阳已经诞生。它似乎害怕这屋子里的世人缺少温暖,就迫不及待的向世人呈现它那无与伦比的力量,与宽宏仁慈的爱心…,…
终于众生沉默了、众生狂热了……
慢慢的,众生在这原本银白的大地上、在这蓝蓝的天空下、在这无垠的海洋上不停的进行欢呼,他们似乎疯了、他们似乎醉了、似乎在渐渐的沉没、似乎…,…
远远的望去,这奇奇怪怪的建筑呈现出一种博大精深的样子,它似乎像这无边无际、惊涛骇浪的海洋那样令人生畏。天空也金黄金黄的,似乎在不停的向大地输送它那最强的音符。
它神圣,它享有这世间用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最大极限,它令世上的人顶礼膜拜,它…,…
风被烤焦了,红红的,就像鲜红的血似的流过这金光闪闪的大地。亮绿的树叶也光彩夺目的,似乎也在慢慢的幻化成那片片的金叶。
我轻轻的向前飘着,在这金黄色的光芒下他似乎也被融化成那袅袅的青烟…,…
十一
风在轻轻的吹着。慢慢的,四处飘浮的我似乎也变成了十多年前的他。这时光不知怎的,似乎一直在不停的倒转。我似乎也在一直血肉模糊的向前爬着,爬向那神秘的建筑,我似乎比他更渴望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的身上似乎有着更多的那渴望血腥的味道的天性。
我沉没了。我慢慢的走进这个奇怪的建筑,它似乎有更多的符合我本来的天性。我是天生的奴隶的坯子和“英雄”的模具,我有着那极度的自卑与强烈的自尊,这两者似乎都是我那奔腾不息的血液与不停颤泣的骨髓。我走进去了,慢慢的向前走着,典范似的大门静悄悄的开着,它似乎允许每个人的自由进出,它似乎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慢慢的,我走了进来,迎面而来的涂满白色、光线如雪的走道,往上再走几步,回环往复、狭窄的房间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向前走着,慢慢的向前走着,似乎没有丝毫的犹豫,就这么一直向前走着,也不知走了多久,我就站在一个不大的房间的门口。这时,我似乎再也鼓不足勇气向前迈步。这房间似乎很特别,仔细看上去,它似乎像一艘古船的造型,再往里面一瞧,这房间似乎被分隔成一个个四方形的小盒子,盒子的颜色是外面涂满着黑色如夜的漆,里面装载有那苍白的面容,在盒子的外面包裹着像胭脂一样鲜红的色泽。非常好看,这似乎是国人的习俗。我不知道的是,我将要钻进那个盒子,那个盒子又适合我了,我徘徊着,苦恼着,在外面就这么一直站着……
不过,我似乎听见那悲号的哭泣声,轻轻的,尽管是断断续续的。此时,风轻轻的向我吹来,远远的听起,它似乎像一首安魂曲,在安慰那已逝去的亡灵。不知何时,这微微的风似乎变成了一种神秘的白色,它似乎有着一种极强的腐蚀味道,这腐蚀味道似乎是在慢慢的浸透入这奇奇怪怪的建筑里面的每个亡灵,它似乎更像生命中的水一样轻轻的、渐渐的在你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是一种不经意的感觉。
十二
“一具化石已早早进入了冬眠。它是不是已成为你的全部所有”?
“你是不是像它一样喜欢沉睡于这神秘的地下”。
我真的不明白。我想,“这儿或许还有你留下的轨迹、你那美妙的梦想与不朽的理想……”
“难道你真的再不愿让这浩渺的空间里回荡你那曾有血色的影子。要知道,你曾经也有过那奔腾不息的血液,不要忘记,它也在这飘渺的时间与虚幻的空间里流淌过”。
“在岁月的长河里,这深深浅浅的痕迹难道不就是生命力在无际的边缘线上留下的那缕缕回音”。
“我想,那就是鲜血流淌过的温度、那就是理智与情感在生命线上的挣扎、那就是曾经有过梦想与理想的见证……”
我知道。“那时的你常常独自一个人在泥泞的沼泽地里前行,我更明白,你曾在那影子般的岁月里,用不停的幻觉来表达你已实现你那诱人的梦想”。
“可是,此生的现实”!
我已无能为力了,只好躺下,我不想再往前走了,我似乎已没有前行的勇气,总之,我是想休息一会,睡一会。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再往前走,我躺了下来……
十三
这时光不知怎么搞的,似乎一直在不停的逆时针转动,飘浮不定的我似乎已无法追赶不上这逆时针旋转的步伐。不一会,我似乎已耗尽所有的力气。我已跑不动了。我已无法追赶了。我似乎只有气喘虚虚的坐在这潮湿的地面上。我想,我是落后了吧,像是已渐渐的被抛在后面。我似乎已无法追上。
它似乎已渐渐的在从我这苍白的脸颊上消失,它就这么一直奔跑着,像似在追赶着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一个幽灵的影子、一个已成蒸汽的云彩、一段划过痕迹、将会在前面等着,那前面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离现在似乎已有二千多年了,是一个如烟如雾的时代。所要到达的那个地方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黑色如漆的隧道。它的里面一直在流着鲜红鲜红的血,似乎在不停的流着,似乎永远也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一股的血醒的味道似乎在不停的向前飘,此时,它似乎已成了空气的代名词,已是你我生活中的必需。黑色似乎也在不停的向前飘,似乎已是这时空的主宰。似乎这里的空间,这里的时间已没有了所谓白昼与黑夜的区别。
不知何时,你似乎已来到这段空间、这段时间,你似乎已是这段空间、这段时间的一员,你慢慢的向前飘着。慢慢的,你似乎已渐渐上升为它们的主宰,你似乎像是在给住在里面的人制定所谓的规范,形成他们所要遵守的习俗,你似乎已飘到这所谓的最高层上,已座到供奉的神龛上,已成为顶礼膜拜的主神。向上看去,座在神龛上的你是一派慈爱、宽厚、内敛的样子。你那曾经如锥子般的目光似乎已平和了不少,长期的养尊处优使你少了许多的曾有孤傲之气,那曾有的青春激昂的血液似乎已渐渐冰冷,犹如那冰冻于海的雪山。
分享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