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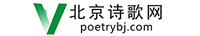

龚纯近作选最主要的有棵开花的桃树(组诗)
龚纯,常用网名湖北青蛙,潜江市高石碑镇曾岭村人,现住上海。出版诗集《蛙鸣十三省》《听众,小雨,秋天和国家》二部。野马渡诗歌雅集成员。
最主要的有棵开花的桃树(组诗)
只有那种蓝在湖上慢慢地道晚安
一整天,都是那种蓝。那种月氏、匈奴、乌孙、柔然
出现过的蓝。蓝得惊心动魄,又澄澈安宁。
其中天空里的蓝,养在水里的时间,极其漫长
也极为短暂,很快蓝到黄昏,蓝到夜晚。
蓝得在若干年之后,你还记得
你舍不得离开,仿佛湖水重新给予了一种生活:
激浪拥堤,七彩净海,羊在羊圈,星星
在马厩,阿尔古丽在毡房中
天空有种无声的深邃的蓝,静静地向你道晚安。
启明星
小时候,我就见过那颗星星
在东方黎明的夜空中。
其他小星无一不远去,只有它自己
留在自己的位置,独守寂静。
澹泊与灿烂交相辉映的时刻
远未到来。天空与大地会为伟大事件作准备。
四十年一晃而过,再见那颗大星浮现天边
我在我的生活里一事无成,已然老去。
希望和指引,乃至想象却仍旧悲伤地
存在于老朽之躯。
光明与热情,将永远献给
这个不停涌来泪光与潮汐的世界。
——我惟一所爱,将永远是
我惟一所爱。在黯淡世界不可垂直的表面。
布谷鸟在上空
深广的夜里,我在等待这个声音
它曾经是善良的提醒,如今
徘徊四方,它变成孤苦无告的岁月催逼。
由南至北,飞越人类的良田
浓云之中,张开大嘴骤然狂啸——
侧耳听,那狂啸仿佛是律令,又如一声声道歉:
永不复来的爱情
早已埋葬千载,郁郁麦地并无半条人影——
古代的良人在荩草底下睡眠。
只有我当今的友人西辞弹着吉他唱着歌,说夏天的后面
还有夏天
只有我的友人西辞,说,何以销忧
可饲养一条胐胐。
闭着双眼,我能看见剩下的一览无余的三十年
杜鹃破旧而新鲜的回声,响彻天庭
不可拒绝,它仍是吆喝我走上废墟的权威。
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广种苎麻的那一年
据说那年西方麻料稀缺
外贸局来人像伟大领袖指导昔日的社员
在钟滚垱一带种下淹没村庄的苎麻。
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整个秋天,都在剥离麻皮
把它们浸入河水。
晚上做梦,我们已经长大了,还在重复那种劳作
河水散发恶臭,麻丝变成城里的衣物。
灰喜鹊大量死去,只有几只野鸽子站在电线杆上咕哝
继续跟我们一起,在村子里生活。
我能感觉到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好的夜晚,黑暗
而平静。有时月亮清亮
好像可以让所有巡逻的树木,悚然站定。
好像可以教人亲吻。
仍然有鸡鸣,像古代中国那样。仍然有牛哞
留下牛屎。
仍然有农妇,喝下农药。仍然有伯劳消失
又归来,大约还认得我们
这些农民的面孔。
逢老集:遥远的梦想
近年劳累,尤为疲惫,多倒头即睡,睡梦难得。今值端午节假期,在家喘息,天阴凉爽,午休于家床,得梦一阙,涉之无穷未来,其中颇有新词而无解,其间于田畎仰望新人类,唏嘘不已。特特记之。
麦秸堆积,几乎就是象山
几近于泰山,没有一个外国人。
理想青年步行其上,热烈谈论
杰作与鸿图,得出“金子结论”。
麦地广袤无垠,宽阔平坦
其中古树参天,有三百首诗意。
我暗羡这世界阳光朗照绿阴庶地
仍有村子静谧,安顿身体。
我暗忖这群少有的青年男女
生于“第四平世”,也有半百年纪。
机器人遍布安宁的田野,晚霞
烧红乡闾,窗玻璃上压来沉重的机群。
我好像在接受战时动员
环顾山河,都是怀沙情绪。
哭腔
突然想起江汉平原曾有一种令人
荡气回肠的哭腔。
离世的人被放在门板上,哭丧的人远远而来
也许是出嫁的女儿,或者是年迈的
姑妹,跄地而诉
抚柩而哭,直至坟墓。
有时听得入神,觉得这是人间最好的音乐
和人类情感的光辉神殿。
现在,这种情景很难再现,很少有人会拖着
宛转的长腔,对亡人诉说遭遇。
人们大约已肉身倦怠,审美疲劳,情感深度
也不配这种动荡肺腑的技艺。
昨夜,我看到一两处祭奠逝者的鬼火
火舌翻滚,没有一丁点声音
——很快,我们就结束了与离世人的各种联系。
站在油菜花开过的地方
站在油菜花开过的地方
天阴,好像田野刚刚得过一场沉重的热病。
太晚了,去年燕子已飞回,重新熟悉
农民远去的绿风景。
我们仍未更换古老的屋顶,还是那三朵白云
有几处恋爱的地方未插入钢筯。
有一些人爬上大树,当自己是片树叶
以为来年春天还可以被看见。
而那些细小的蚂蚁有时也发动大面积战争
只有小孩留意它们遗弃的尸体。
只有小孩来到城市才发现自己的出身
反复清洗自己的泥腿子。
此刻,我的脚趾有些发臭
一棵李树正在身边,失去香味。
哟哟伊哟呀嘿伊嘿咿呀哟
仍然是油菜花开了不顾一切
仍然是我孤独地回返家园,仿佛是来为看风景
又仿佛是来临危受命。
平原上有三个瞎子,要出远门
从大军山回来孤独终老的舅爹
缩形于一圆形瓦罐。
有人曾在土地上送我苹果,有人
递给我一块钱币。父亲和大伯挑了几块骨头
给上一辈子的人移了坟丘。
桃花开得猛烈,油菜花开得不顾一切
一块猪肉下了油锅
平原上升起孤零零的人烟。
平原上的三个瞎子还是在小时
就是三个瞎子。三个瞎子分别是道筒、二胡
和钹锣,但有时是板鼓,有时是化脓将破的长笛。
吹吹打打,热闹啊有时桃红柳绿寂寞
肝肠冷。爷爷奶奶姑姑婶婶
起夜喝碗凉水。
仍然是人间三月,天雨,站花墙
女子失去爱情。我听见三个瞎子唱伤心的歌
先是铺天盖地,后来是安静悄无声息的月亮皮影戏。
花园
这里看见银杏重新返绿,天地纯净
晚樱花落得不像吉野樱。
坐在石头凳子上,迅速地成为一名老者
打量这复活的世界。
可能还有比我年老,或比年轻的“领军人物”
带着鄙夷他人的恶臭嗅探着中国诗情:
甚至阳光都是污垢,甚至古老的汉语都属贱民。
这么着吧:戴胜鸟飞行途中,排出一坨稀粪
砸向人们的头顶。
我想到这些:他正在为某种心头恨而挣扎
他也看到繁盛的花园,他没有足够的思想
身体放在花瓣上面。
一直记得
那年春天,走在油菜花田中,他
还是一名无人爱惜的少年。
从他的衣襟看,能分辨他所处的朝代,那着装
就像日后的爱情一样破烂,但一直记得。
我们没有更好的安慰给他,他在他的世界里拥有他的一切
而且那时他还不需要一个永远忠实爱他的女人。
而且日后也没有一个永远忠实爱他的女人。
太阳寂寥,不需要叙事。
风中,有棵香橼树。有棵枣树。最主要的
有棵开花的桃树,有河边描述了也无用的垂杨树。
岁月给我带来很多东西
一个年轻的女孩问我,他是不是坏蛋
事实上她已坠入爱河而他毫无疑问
是狂蜂,花朵上的游客。
他们频繁见面,在草坪假山前
有时沿着湖岸散步,去到小树林中。
亲密关系的痛苦,不是惺惺作态
而是伴随着身体的欣喜与,不由自主。
他们活在全新版本的世界里,爱情
似乎为涉险而存在。
诗歌贡献谜语,源源不断地带来偏爱
伤情与孤独。
此时,2018年5月12日星期六 23:58时
听到布谷鸟鸣叫,在上海,嘉定
安亭,楚国人黄歇安营扎寨的地方。
它远远地问我,中心摇荡,是不是神魂
没有看守。又或者
形同几年后她对他了无挂碍,是不是
另一种形式的,死亡。
谢克顿作如是想,一个难以平息的
淬炼成钢的意志锐利生成:
我的个人情感没有被最终破坏,仍以碎片
方式得以幸存。即便游客归来
我也会老实作答,她已经永远地离开
岁月给我带来很多东西都已被拿走,但以我
越来越老,作为补偿。
与双亲国庆节登襄河大堤看汉江兴隆大坝有感
年近八旬的父亲,七十有余的母亲
爬上他们曾经维修多年的
襄河大堤。
一辈子劳作的人,闲了。故地重游
好像辨认老朋友,变得
陌生的面孔。
江堤上,分布着吃草的牛马。天空中
分散着连绵白云。
面对江水,我们正在回忆它们的过去——
民国和建国风潮退去
方始平静。
再次开挖河道,修筑兴隆大坝,拦截襄河
让河水流向北京。
我们以为,跃进河里的水少了江汉的养分。
我们还能怪谁。这辈子所建丰功伟绩
绝非一人之功。吃过的苦头
已经没有痕迹。
大堤逶迤,不可用以抵挡漫漫
年老的寂寞。
东流活活,到头来已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细沙沉积。
特色,主义又渐次无人提及
只有农人依旧收割田里的稻椒玉米。
只有父母老去
只有长大的儿女归来,在阳光下,在暮色中
伴双亲闲走于乡闾。
纪念同学聚会而描述高石碑中学旁边兴隆河堤岸上的水杉
少年时代末端的那棵棵水杉,并未从时间中隐去
它们排出永久的队形,上课铃声影响到它们:
已经发生的事情还需等待时机。
小风在枝桠间缓缓移动,有时助杉针长长
有时,树叶款款飘落
读书郎与林间鸟,各有各的位置各唱各的歌。
有男孩女孩在树上刻下俩人的姓名
多少年后,这俩人在自己身上
逐渐清空班级里其他一些同学的名字。
这些水杉树站得久了——没有人的房间
也没有人的距离。多年后,你懂得
青春年少没有多少理性的成长。
从座位上起身,跟他走进林中去
好像有两条路属于我,和你
她的脚印无穷无尽,不是渐渐由陌生到熟悉。
多少年后回过头来,寻找曾经的集体
似乎只有我一人会走小径
穿过那么多年前的梦境,没有契约,再无心迹。
林中仍在下雨,因自己无法解开的疑窦
迂回到青春时代的始端:
重新踏入湖北潜江高石碑中学的门槛。
又望见老师紧盯的眼睛,课本,习题
望见杉林上方一动不动的白云
仿佛时间依旧,世事变换都属乌有。
女同学
她点亮煤油灯,移向我这边。
她低头,并未看向谁
拿着钢笔手掌支着脸,想她的作业。
她皮肤,是熟麦子的颜色
她笑起来,两颊荡漾出动人的
安静的酒窝。
那时,现在,古老的酒窝也极其少见。
许多年过去了,我好像忘了她的名字
只记得那笑靥。
煤油灯下滋生的无声喜悦。
我还记得我穿着破棉袄,和牛车上的书箱行李
一起回到高石碑中学。
记得台灯没有油,但不缺师长,风俗和
规矩,善良与贫穷。
我世间极其美丽的女同学,一毕业
就没了音讯。
几十年一晃而过,在极其短暂的春天
我想起她来了——她叫常英,董芬,罗振红
董福珍,史湘红,熊想英
类似贝德丽亚采,格丽琴。
她一定在别的地方
微笑着
阳光照彻,傍晚带来一轮明月。
豌豆巴果雀子叫了
记得小时,我们称过端午节为过端阳
称布谷鸟为豌豆巴果雀子。
因为识了字讲了普通话,如今我们的方言
丢掉了许多说法。
我叫父亲为大大,喊母亲为婶娘而不叫妈妈
现在,只有他们还叫我乳名。
五十岁了,大大还在询问我是否学习,吃饭穿衣。
电话中,父亲提到他八十五岁的兄弟
看他来了。
也提到我的兄长,他的大儿子周末的晚上
送来几尾河鱼。
豌豆巴果雀子该叫了,今年我还没有听到
在苏中平原,在叫做上海的大城市
没人同你讲家乡话。
内心里你同自己讲,讲的还是潜江口音
你想起的时间,还是江汉平原土地上的耕作日期。
你仍习惯称柳树为杨树——
“飞杨花种棉花”
若是听到豌豆巴果雀子叫了,还是心生喜悦
与惶恐。
在这些日子里,总是担心天气突变,刮风下雨
误了插秧割麦的最好时辰。
几十年过去了,我早已不在那片土地上耕耘
但这颗农民的心房
还未曾变动。
童年记忆
当我小时,村子里还有几座开花的树林
桃李花事繁密,竟无人欣赏
大片大片的麻雀,鸦鹊,几十成百上千亩鸟翅膀
驱离又飞来,在水稻田,在瓜果地
令看田的泥腿子苦不堪言。
我们的牛棚,往往要分管几头身躯庞大的牯牛
它们常常发现,并拼命于其它威猛的对手。
疯子何林大约五十岁?他跟我们一起上学
曾得军老师家回知青点,弹琴煮粥。
国平的泥匠父亲,抹灰砌墙架屋
简直是一方权威万人称颂。德全老头断了气
人民公社给坟墓。
追悼会上,老妪新妇痛哭旧社会然后中年人
敲锣打鼓,抬棺埋入泥土。
菊芳姐从他乡嫁来,塞红包,撒糖果
几个无聊汉偷听墙壁,又如夜鸟被惊动一轰而散
惟有西厢欢唱的虫子,能喝沉重的露水。
我六七岁生鸡毛眼,入夜看不见东西
八九岁,学游泳,死过几回。
不记得情杀,不记得溺婴,有时我父亲奔行十余里
会为三五元钱,求助于远亲。
走亲戚
嗅到一股放肆的气味,两棵臭椿
站在门前,那么高大、笔直
仿佛不知道自己的味道。漫长夏季每一种树
在风中都留有一团飘浮不定的阴影
奶奶的姐姐从阴影里迎出来
用她的金莲
她们搬出竹椅,坐在廊檐下说世上的事
我所知道的世上事,是如何抓到臭椿上的瓢虫和
不知疲倦的知了。她们说着说着哭了,拿衣角抹眼泪
屋台高,缓缓走下台阶就是河水
阳光白得耀眼
除了三五只鸭子随水漂走并没有什么走动
后来亲戚们陆续出现了:大姨爹,二姑爷,二婶
三娘,秋生哥,蓝衣姐,甚至还有一个
叫春妮的妹妹
我和春妮无事可干摘了些木槿花丢到河里
傍晚时分,大岭生产队的广播响起,依旧是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听领袖指示
像唐朝的百姓得到伟大的李世民,带领我们
在国家崇拜中寻找安宁
灯火依稀,天上亮着星星,看这人间忽远忽近
至亲之人陆续故去
这是埋入土里的:世间的酸涩、不平和冤屈
这是四散开来的:从熟悉变成不知所终的陌生
烈士
父亲去世前一年,回忆一名
村里的青年
他的心、肝被村公所的人炒着吃了。
他们抓住他时,他的衣裳上下
打着许多补丁。
他有几两力气,年轻的肌肉被太阳
晒得乌黑,和土里八叽的农民没有两样
不像共产党员。
他们拿了腊贞家祖奶奶的铁锅
下面用木头加猛火。
他没有成家,也没有田,他兄弟
他兄弟的儿子孙子几十年里为他争取烈士之名
终得于二零一二年暮冬之际于长市镇
曾岭村跃进河河堤竖起
正名之碑。父亲告诉过我几回
我始终不记得他的名字。
他们问腊贞的祖奶奶,很好吃
你要不要吃,给你留一块。
泥藻集:诗歌常数
有谁研究过铺天盖地的麻雀
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变成“四害”?
我们非常幸运,精细结构常数
仍是1/137,有谁指认这是天大的谬误?
诗歌仍是我们内心生活的主要形式。
有的人螺旋体暂时有些松动,无论如何
脸色苍白,但不会变成大鹅。
有的人心中火焰不再炽烈,那也不是
神秘主义不得入门。不管负多少次
情伤,总有人力劝诗人全神贯注于诗艺
与物质。就像我本人,不再泛起
十年前那种被无数孤独追赶而泛滥的
自恋情绪——数量无多的麻雀
有一种非历史性的天然回归,它们
认领常识、良知与内在经验
为公允不可或缺的领地。
棉花地里的事情:远去的村庄
秋天生出许多芦苇。水沟里长出藨草
与蒲苇.芦花妹妹,在河滩边闪现。
我们的芦花妹妹,后来,后来
在互联网上修改了姓名。有时
站在外白渡桥上看风景。
起雾了,亚洲第一湾在外滩消失
流着泪,喜爱上另外一个人。
花心萝卜,炒来吃必定有些苦涩滋味
镜花缘中,爱上这么多个
叫得出姓名来的女子。
只有我们的村庄还是那么忠贞
冬天的大树一直没有移动位置,猛起
一阵风,将它的叶子卷向不可知的远处。
远处,河堤细小,夕阳巨大。
仿佛有人将踏夜幕归来
经过无数岁月,迷茫无措,安宁的等待。
菊花铺满小路,光阴仍在倒流
书包里,装一把上学路上吃的豌豆。
除了伯伯三叔,哥哥二舅,班上的同学
不会遇见后来的那么多的男人。
春天邂逅的小蛇,到了秋天,已有婉转的腰身
冬天仍会遇见一些,日常在她身边
聚集的鸿鹄与,雀类。
我们的芦花妹妹,仿佛一个刚刚醒来的梦寐
清晨的村庄,听见人声,不见人影。
我有一个名字
叫忠孝。又叫
柳梦梅。
平原落日
天一下子就黑了。出巢的鸟又飞回,流出的水
经过夏日的桥墩。
夕光远照树林,小风模糊不清。
亲爱的,你是怎样一个物体
记得你从荡漾的湖北升起,荷叶盖住了我的头顶。
穷人家的竹杆一早撑到西塘,问姑娘看不看得上
风中的花布衣裳。
大舅背着竹篓,走向生猪市场。劁猪客随手把猪卵子
甩上兽医站的屋脊。再走五十米
是药铺,收半夏半豆篓,收蝉蜕两豆篓。一块零二分钱
让小人感觉富有。挑三拣四,买得
一角二分的娃娃书。
试刀口,抡把式,两个铁匠把他们的主顾丢在一旁
只管钉钉锵锵。
五个粑粑称为一斤,需要全省通用粮票。
红糖三两,裹上地主帽似的扎纸。
街角上长着两棵榆榔树,和一棵慢悠悠的槐树
一分钱可喝小桌上的茶一碗。
有两铁门的,是农机维修站。大屋檐带五星的
进进出出的都当官。
不打补丁的衣裤比自己的漂亮,穿凉鞋的比自己的赤脚
不怕土路烫。
往回走,水波不兴。往回走,秦桑低绿枝。
往回走,金陵无酒肆。
亲爱的,往回走,你慢慢慢下来,现在我可以把你
当媳妇对待。我媳妇红光满面,我媳妇
在远方徘徊。我,早已经不是
那小屁孩。
劳动,等于远处之物。歇息,相当于每一户人家
都有收回来的视线。
煮粥,切空心菜,倒泔水,打扫堂前台阶
听蛙鸣,一窗落霞什么时候
被抹得干干净净。
钟滚垱奏鸣曲
听说,某人为一段失魂落魄的爱情
写了一封长信。这封长信一直追随她直到
她将家庭地址变成一片麦地,上面的每一个字
都唤起过时的柔情。
某人剃去黑发,下巴蓄起关云长般的
长须。她早早起床制造了面对旷野的背影
夏日远云就像寄来一份贺礼
他们再见已换地点,有只铜铸姬鹟跳跃其间。
几十年浮萍南北,复归乡邦,小池塘荡着
旧友般的情谊。他废除了到达她的权力
他站在旧屋顶上高喊:日西方暮,其可图乎?
——然而只是风大,纸上并无任何字句。
仰望月亮的赤脚医生,偶尔也送来病房里的寂寞
天空已老,多的是自伤的夜晚,失去
爱情的长期体验。曾经的少年啦
曾将某个日子刻上某棵树木,某块石头。
今日寻思一位恋爱的女子,只有婚配连着子宫
记得频频于梦中发生怪事:谢克顿与始皇帝讨论
长生不死的问题。某人!老境将至
麦子即将成熟,每写一首诗,都怀着不能胜任的寄托。
夏日白云的到来
坐在窗前看白云,感觉我们在同行
心里知道,不会同行很久。
开始我以为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缱绻之情——
很多很多,珍贵无比。
就像晚来的白云大面积涌现,落日恢宏
壮丽,如同不可更选的福祉。
一切想象都良善,一切匆匆而过也属好心——
白云自然无法巧取褫夺。
白云自然无法为谁恒守家乡与灵魂
就像提出忽然增多的要求,就像无所适从的圣手
美德与苦行,前后推辞与失矩——
白云在身上移动,人能年轻几岁?
白云并非我们真实的领土,干涉极为愚蠢
故作轻松散去,才可避免颜面扫地。
我曾以为我太过幸运,觉得白云带来深情——
它使天空蓝得要命,就像头破血流人也要站立。
我曾经那样憨直,不着边际——
如今远远地看着,充满怀念般的宁静。
回乡
列车飞驰,阳光渐渐加强
……我的心在轰鸣。山脉沉静。
山色一览无余:这中央的山峰尤其美丽,大白天
它宁静而多云。
那车窗外平整的土地,被阳光照耀的草木
这时候,已经黄得可以。
它们既不是祖国,又非故园,就好好地放在那儿吧
我最不能放下的,是刻不容缓的郢楚情思。
阳光几万里,经过几个省,现在进入亲爱的湖北
亲爱的潜江。风景和往事一一敞开。
有条河流已经朝我流来,长江汉江和她们永不停息的支流
在我亲爱的家乡,和我一样,在我朝思暮想的土地
深深地行走。
(编辑:张坚)
分享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