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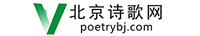

外星人自选诗四十五首
Alienhu 2022-09-11 12:49:52
第五届国际诗歌奖:外星人自选诗四十五首
在病房中听见斑鸠的叫声。
梦境中满是精细的装帧
彩色灯管,和众多活着的
死物
我无法入睡,伴着汩汩的
气泡声一路清醒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千百回
将死,或继续勉强苟延
不容细想
这是最冷的季节
摩天轮在寒气中远远地发着
散淡的光
游乐场仍在营业
我怀念那个没有头绪的
萧条时代
那时的“死”还未被打上引号
以梦为盖。
有时深夜失神地触发
无端的下坠
像瞳孔底部不可见的光
人们睡着
有的仍不甘示弱
她们以密集的死亡做意象
往同一个方向
快速聚拢
落在牛皮纸上
竹节上,墟烟上
湖中汩汩传来的游水声
有时以梦为盖
沉在大丽花鲜嫩的蕊上
痴人。
我贪恋的是宿醉
鸳梦与白描,青蛙的卵
爆裂
汽笛的波谲放浪之声
我贪恋的是圣像的灰
一步步向上塌陷的虚空
这个冬天最终流放
我们无法安睡的荒芜
止境,炼金术
我贪恋的是一切的现实
与假花
帮凶。
我们在白光下一同噤声
使那走在人群最前面的人
孤立无援
默默看着她跳入空场
如绞杀的猎物
再也无法转身,我们一起
向她发射子弹
咬紧牙关
我们装作听不到她的哭声
和惨叫
林中继续的苟且与宴饮
像所有被侵蚀的钢铁
即使是在四月
战栗的或苍白的
将死亡的黏液,涂满全身
吞炭为哑
或许我们可以,侥幸生还
小镇往事。
我通常把日记放在床下
而不是色情杂志
阿姆依然在CD里念叨着女儿的名字
蝴蝶啊蝴蝶
我笑着拔弄食指上的虫子
我不是个乖孩子
这氛围再妙不过了
肥东尼没有化一脸诡异的朋克妆
在我的面前做爱
最好再来一罐蓝带
天哪 我已经七年没失忆了
这真棒
妈妈偶尔会来看我的
我,偶尔会想起凯丽,那个离别的
早上
记得那天看电影的时候
我吻了她
接着我的狗狗克罗基特就被汤米
装进麻袋浇上汽油
烧成了炭
或许我真的不该吻他的姐姐
这可真糟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
肚脐旁,那个被烟烫伤的疤痕
还在
还好这是七年前的事了
在一个垃圾场里发生的,破碎的
细节
我忘记了该忘记的
振翅的蝴蝶
老掉牙的录相带
那些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光阴
如果只是一场梦 该有多好
甚至凯丽
我不该将她独自留在那个, 偏远的
小镇上
任其腐烂
后来有一天
汤米打电话过来,恶狠狠地说
凯丽自杀了
有一天我也会的
致我。
火烧我
如提炼稀有矿石
淬我
日复一日的捶打
在温热的风里
收起自画像
归拢翅膀
致我夜晚的悼词
凿壁偷光。
我要到达的世界
在这堵墙的,另一边
一个小小的孔洞
所能透射的微光
足以令我看清,它的
样子
足以令我深爱
足以令我眼含热泪
足以令我,全情对待
当这轻柔的暖
映照在我年轻的
脸庞上
它也该俯身看清了
我的样子
我是个,想去撒野的
坏孩子
我想拥抱的后花园
在这堵墙的,另一边
飞向大麦哲伦星系。
这不是我们的句点
我们的尽头不知所终,但不是在这里
不是在那里
也不是任意一只,随机落下的松子
砸出的坑
只需记住钟摆的样子
那些转世的明灯燎出的火焰
还有多少未曾读取的,信札与花丛
我们熄灭吧,像最初我们点亮什么的
时候
在光的阴暗面,在真空的气泡内
在视线的盲区,冻结
留下无数的针眼
在蝴蝶的断翅上,写下剩余的怂恿和
口舌
我们这就暗下去吧
交出所有的卵,或以卵击石
交出所有的凹槽,和清水中的刀片
我们只有一个航向
从一堆沙子到另一堆沙子,从一粒盐
到另一粒盐
星际讯号。
我发出的死亡讯号
你们都听见了吗
我不是第一次发出死亡的
讯号了,今天
我又向人群中
发出了我的死亡讯号
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
发出死亡讯号
除了涂鸦,这是我
唯一能做的挣扎
看那些暗下来的墙壁
条状的倒影
那是我又一次,向你们
发出死亡讯号
十万枚钉子。
一个人用十万枚钉子,排列出影子的
形状。而我,只需要一枚就可以终结
所有的幻象
一块锈迹也可以,一条划痕也可以
一个跌落在地的叹息声,也可以
在麻绳织成的坚涩墙壁上,只有黑猫
充满警觉地吸附着
它悬挂在其中一枚钉子上
仿佛衔住了一截无声翘起的冰冷的
阴茎
再紧实些!你看啊,脚下那些虎口与
深渊。在灯下
橡木是屡屡痛哭的看守与伽倻琴
它需要这十万枚钉子,从空中闪电般
下落,刺入每一条纤维与纹理
所有的榫卯,楔子,嵌合,与行割礼
都必须不遗余力地产出、进行
所有的念头都必须,牢牢钉住
如困兽,即便这时响起十万只蝉鸣
它们也会撕碎一切
它们会燃烧殆尽,如喷薄而出的熔岩
它们会爆烈,如沸腾的血花
这十万枚不停发出嘘声的钉子
就是十万支弹动的箭蝗
十万亩精细的松节油
十万吨雨水
它们死死钉住了脊柱上每一条凿痕,也
钉住了,所有的灰烬
塞尔维亚人。
箭最终没有射出
此刻她站在圆形剧场
不太激进地发声
她被人们环绕
被听见,被伸出
被小心翼翼地
收回嚢中
她先是
蒙上我的眼睛
而后将自己的目光
校准
向我盯视
我钟爱她坐在
骨堆上
木然地擦洗血迹的
部分
易耗品。
每当我用掉一个梦境
就崩塌一个远方
每当我向天空索取一首诗
就熄灭一个太阳
秦腔。
它的声部类同于某种尖锐品质的摇滚乐
我赞成某个乐师的荒诞说法,但不赞成他的
表情
高亢而无衰变是它的特性
我们熟知振动中的每一条纹理波峰浪谷的起伏
睡梦中寒流通体般的震颤
为此我设定凉棚中要出现旱烟的丝和一副
面容模糊的山羊胡
不设蓬荜,不设报幕者,不设精致昂贵的
金属利器
唯有花腔尖脆
越过粗厚的矮土墙往荒野之中疾行
烟雾悬在横梁上久久不散,濡湿中杂乱的
眉眼,场景是拙劣固化的泼墨山水
他们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动作,高音如提琴的
绷弦渐入但毫不渐隐
铜锤是双刃,油彩是虚弱的遮掩
羽毛和盔甲黯淡无光。我们恐惧散场的发生
如高维跌落
弦断了,我们深知散场即将大雨一般降临
其中一颗星星。
在所有跳动的光芒之中
你不是唯一的沙子和坚冰
在所有环绕的黑色之中
你不是唯一的沦陷和渣滓
你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
颗粒,或点状物。或许
你就在天鹅绒的纤维之下
消寂,生息
如故去的
艺术家笔尖滴下来的静物
或明或暗
在遥遥遥遥遥遥遥遥遥远的
大麦哲伦星系
我们的祖先曾到访过
每一颗明亮的新星
而后他们放弃了,永生的
机会,返回到了起点
他们卸下了皴裂的角膜
指甲上的白月牙儿
骨骼中的盐粒
按照行进路线的,分布图
建造了世界,和所有的图腾
行星的灭亡。
这醉倒的三千国度
这佯装沉睡的三千只
未命名的孽种
它们只能在心里咆哮
有时连沉默也被定罪
它们生于风暴中心,就终将
死于痛哭
这拥挤的泥浆
要尽可能多地裸露,下陷
或呈糊状缓慢地流动
它们猎杀
耕种少年的荒淫
废冢之间游荡的磷火
烧灼,如鲜红的马蹄铁
逆生的毛发令人羞耻
真理的检验需要借助足量的
火柴棒和鲸须
它们不是唯一的反骨
拷问也是徒劳
更多的毒品将被合法化
更多的妓女将一一沦为良人
还有更多的雨水将会垂落
在巨大的忏悔室
永不间断地播放着锯齿状的
安魂曲
它们随着旋律无声地起舞
同时又面无表情
嗜睡才是其中最美的段落
这三千重扼腕的国度
经过万年的冲刷
却从不曾减少体量
犹如长久负重的前列腺
只会肿大
唯一不变的是它们那,散发着
金属光芒的手势
它们必将终身荒废
它们只有一种可供呼吸的方法
一面无穷建造
一面永恒崩塌
不要轻易与死者交谈。
我的体温
死者是无法感知的
纵使在烈日之下
它仍固执地报我以
彻骨的僵直与冰冷
它不说话
这一刻万物凝重
但它是最轻的那部分
最不屑的那部分
最暗的那部分
它正像我肘部多余的
角质
一样缓缓脱落与降解
它绝无法感知
我那些一直深藏在
虹膜之后的凉意
正如它漠视我的体温
它无法感知我的悲怆
与安危
它无法感知兵临城下
它无法感知唯一的
已崩的脊骨
它向着虚空重重跌落
带起的风声打在我脸上
这一整个下午
我能想象的刀锋
莫过如此
我们见过的黑夜。
我见过的黑夜
与你见过的大致相像
不同的只是星空的
分布
和雨滴的数量问题
在所有我享用过的
餐桌旁边
唯一存在的是渐渐
隐去的,众多的脸庞
除此以外
我见过的黑夜
与你见过的大致相像
草木皆兵。
没有下雨
那是几天以后的事情
葬礼也是
没有什么能让我
直立起来进食
我的凤仙花
还不够鲜美,多汁
草茎中的虫子在酝酿
一个国度
人们在觊觎飞行
这门技艺
我机械式地查看
每一滴血液
每一丝风声
每一个食不果腹的夜晚
人们都
草木皆兵
幕间剧。
在人群中
蒸腾的热气会让人矮下身子
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
有时会恐于深入
但我知道我离不开他们
如果失去我或是我不在其中
那个漩涡会照样转动下去
那股黑色的空洞的力量一分
也不会减少
这是致幻的部分
我不得不在此止步,退回水井
旁的一次小聚
或葬礼上的消磨
星尘。
真空中是没有声音的
我们的声音需要借助空气
才能,向外传导
我正醒着,环顾着群星
我环抱着你
轻轻踩中一粒灰尘,往后
翻转,退去
你要睡着,忍着剧烈的
腹痛
像困守一座宫殿
这时,让我带你做一些简易
飞行
必要的时候,我们降落
木星,及其它星辰。
坐在桌边发呆
良久良久,始终
没有勇气翻开《佩德罗·巴拉莫》
此人是致幻之物
或《夜观星空》
我已确信无法看清木星
我是迎着风坐的
好让头发吹到耳后
肩后
好让它不会打搅我继续发呆
我注意到今天的节气
所以风是微凉的
这跟我阻塞的左胸
是相对的
我想起几只被轧死的猫
与鸟类
陈在马路上的形状
那是一种难以描绘的毛糙而
不规则的饼状
这时有人发来日志
上面记载着她的登船时间和
所有正在进行的
犹豫不决
我可能选择继续发呆
坐在这幽蓝的球体之上
不跟她返回故乡
遗憾无法送她一程
她与我的航向或不尽相同
或背道而弛
但这不是真相
我已确信无法看清木星和所有
其它的星辰
听风的上午。
秋天来的时候,最低的那根树枝上会结出
我的恋人
在这之前她已消受所有的粉末,造出了她的壳
那天有风,那该是一个下午,或沉浸中的
暖黄的黄昏
可以有光从叶子间透过来,也可以没有
我希望有几只鸟鸣偶尔发生,事实上我常在
这样的时刻在此停留,体味
饥肠辘辘,暗自消磨一束小雏菊的身子
如纵欲者
我总是疼痛,或如坐针毡
每到天色将晚,悲伤袭来,湖水层层漫上来
鲸吞的月光
微醺中推开虚掩的门禁,脱帽、束手
向所有的物件致意
我的恋人,她是昏聩中的一道模糊的影像
白墙上的污渍,眉心的疤痕,肉中刺,眼中钉
挂一只纸灯笼吧,我可能需要喘息
尽可能温柔地揭穿我,杀我,使我骨肉分离
善待每一道褶皱,中空的果核
悄悄摩娑,抽丝,与剥茧
在香水铺兜售,与人们消极寒喧一二
或照亮些什么, 发出成串的青草微绽的声音
与火花塞
虚拟画像。
我以为的墙上那幅画中的她的面容是我
曾标记过的
就像我曾细心载入她的呼吸和,步伐
那些雀斑是我拓印过的,发上的那些油脂
是我仔细嗅过的
每一个毛孔,都是我小心翼翼点数过的
在这一秒,我背对着身后的白墙壁
吸纳着一股无形的暗力推动我,将我嵌入
框中,嵌入纸中,纸嵌入火中
橡木框中大笑的她,明媚的她,甜腻的她
在她身旁生长着的绿植与她形成等高的
力场
她望着我,我背对着她
这白雾蒸腾的空虚难制的上午
我们完成了,一次热蜡般的凝缓的变奏与
对话
屏住呼吸。
那是画廊中被注视的夏花
穹顶投射的影子打在凝固中的
雕像上
她是串连着数个季节的恋人
或指环上的祖母绿
那装载着我所有白日梦中的
行走,与攀爬
都像冰块一样无法许诺,轻信
要回到画室中,回到画上
回到不可被照亮的禁区
不可被捕获的星球或孢子
不可被蒸腾的松节油与寄生菌
一切都被封存于镜面之中
叠底,穿透,消融
像硅胶揉成的蜂蜜一样明亮
却不可调和
这是我所有的不安
她仍在向着深渊的白缓缓移动
不会转身
睡前故事。
我能想到的流水不会比量杯中的更多
它的沸腾说明不了什么,相对于我的平静
而言。我更擅长观察猫的瞳孔
一块鲜肉的腐烂过程,一朵金丝菊
我倾向于承认它的枯荣与衰败,它不会
产生果实。
这之前我已经试探过瓶口冒出的白气
那是一种沉重的细沙,与乏味
我总能感知到人们的苦衷,它必须获得
更多的药片
摘星。
要涂抹星星吗
试着
擦亮一只灯泡
池塘边追赶萤火虫
点燃所有的
松脂
与黑火药
告诉人们
那绵延数亿光年的
饥饿,与痛哭
或是伸手
从将熄的篝火中
收集一粒火星
握紧它
苹果和雨滴。
已经忘记形状
随机被敲响的铁皮棚子
栅栏冰冷而新鲜
雨滴精心摆放
在每个落脚点晕散
夜晚向外翻出
像一个裂开的伤口
我们见过的黑夜。
我见过的黑夜
与你见过的大致相像
不同的只是星空的
分布
和雨滴的数量问题
在所有我享用过的
餐桌旁边
唯一存在的是渐渐
隐去的,众多的脸庞
除此以外
我见过的黑夜
与你见过的大致相像
可能的雨声。
每一天都是白活
每一秒都是浪费
每一个夜晚都在使我,更加
消瘦
我生来就是虚度光阴的
进食、排泄,打着响亮的
哈欠,钻进落日筑成的壳中
没有表情,没有骨头
谁能来叫停这一场荒废呢
我早就该死了
或是无论去什么
暗无边际的地方都无所谓
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
除了。。。除了那可能出现的
不期而遇的
雨声
小声呼吸。
神在注视我
当我想到潮湿的夜空
一团雾气
盘旋在大楼的腰身
细弱的雨点
从空中纷纷栽落
我知道
那是神在注视我
瞎子们。
瞎子一生下来就是瞎子
九月的阳光照在他宽厚的背上
那么明亮,那么烫
他却浑然不知
瞎子一生下来就是瞎子
他从未见过太阳
趟过的清凉的小江水
他永远不能准确地说出水流的
形状
手中的木棍是他唯一的依赖
广播,或机器读取声
小瞎子是他的完美复制
小瞎子一生下来就是瞎子
电梯每在15楼停泊一次
你就能见到一回小瞎子瞥向
天空的空洞眼神
如果在夜晚
你会听见小瞎子那被闷在
玻璃容器中的嚎叫
它会准时越过毛坯窗台
向黑暗中层层扩散
仿佛深夜渐进中的某种发作
互生。
这里的每一个我
都源于我
我是一粒粒沙子
一束束散射的弱光
碎成一滩的纸屑
每一片无法拼接与缝合的
毛玻璃
很多个我
每一个我
每一个精心的
脱口而出的字眼
每一个我的
每一声咒骂
都由每一根蔷薇的小刺
编织而成
如癌症杀死宿主
你杀死我
那杀死我的
也将杀死每一个我
每一个杀死我的
每一个被杀死的我
都源于你
与那每日丧失的人群
水滴。
水是从天上来的
以一种特殊的随机形态
落下来
在路灯下
在屋檐下
在大楼的夹缝中斜插
而下
夜晚巨大而冰冷
笼罩着每一间,正逐渐
矮去的屋子
每一滴水都是不同的
它造成了每一片不一样的
雪花
宇宙残渣。
这是众多出神的时刻
的其中一刻
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漏斗
我是漏斗的尖
我是唯一
及唯一的剩余下的支点
与渣滓
在那散射的虚无之处
像一只机器蜻蜓,绕行于
湖面
我对这面湖水进行了一次
巡航
并付诸想象
这是极其庸常的一刻
我留意到湖水悄悄退下去了
几分
观鸟图。
废墟旁有潦草的阶梯
竹林收拢,造成一片弧形的
暗区
有人在对岸抱臂窥我
马尾,睡衣,面容模糊
与条纹T恤的男孩在争执
鸟类充分细化
择木而栖
不同的树木,不同的族群
一一对应
我试图往林中发射子弹
制造事端
不见任何震荡
子弹悄无声息,落入虚无处
如坠深海
更多的子弹也无济于事
斜坡上的竹子戳在空中
纹丝不动
没有表情,没有声音
河面上荡着一层薄薄的炊烟
看不到源头
北风向
顺河而下,易吹散
我记起那个惶然的午后
向村中的女人问路
她顺畅地答我
脚下的废墟曾是一座安宁的
小村
对岸是肖水影
傲慢。
如何穿过一整个宇宙
到达一粒灰尘
仪表盘上所示的并不确切
纷纷落下的毛囊也是
沿途播下成堆的石像
与火种
行歌之迹
这些都无法在黑夜中
留下一丝划痕
有时怀疑
那握住的也许是个错误
完成了一次次授精
声波在真空中不能传递
光照匮乏
但我们仍按照,盒子中所
标注的坐标
继续妄行
梵高自画像。
是血吧
在雾中采撷环状的森林
人脸轻浮
光被钉在墙上
草秸竞相归拢
丧失水份的果子
积聚着糖份
但怅然若失
他在破碎。或试图
向远山
写一封信
途中。
像虫扑着火
士昂扬赴往死地
那一天我们佩戴上假的
眼球
追逐落日
在途中
我们目睹了大群的钢铁
在林中搁浅
霞霭暗沉
星光凹陷
当黑夜塞满了屋子
如火烧四野
虚空将我们重重加持
若感到不安
就死灰复燃
放大胆子
往土中种下一个个气泡
趋光性。
窗帘亮起来的时候
植物立刻感知到了光子的降落
她醒了
一片片叶子缓缓伸展开来
紫的额叶舒张
那致盲的芒刺群的爆发
将被最大面积的接纳,纳入
黏附,融合
雕像般的僵硬,不可理喻
她尽可能朝向光源
当光子渐隐的时候,她收拢
石膏像速写。
浅滩上的大卫
芦苇叶子上的奔跑使他筋疲力尽
佩戴着月亮的
是我们的红衣主教
月光中正铺陈着
他那煞白的孪童癖
他的铁锈
他的涂改液
他活塞式的足弓与轻蔑
于是大卫死了
权杖落下
大卫的名字是叹息中落下的灰
大卫缓缓收住了脚印
黑夜已被叫停
集会。
五月的海明威剪去了长发
那一夜是绍兴路八十号
他随身携带的啤酒我一滴未沾
那一夜
我们被纸张和烟草重重围困
霓虹灯管映衬着法国梧桐
纷纷打烊,我们从此杳无音信
那一夜我们缓缓步入盛夏
长发的海明威佩戴着查理九世的
模样
说书人。
完美的叙事是病态的木塞
我从皮下挤出小水珠
主人以蜡封印熨贴,加盖印章
橡木的洛可可与弯曲
镜像反噬中的死亡在将我
双重拓写
像看管大批耸动的链球菌群
盲从,陷入恶臭或献身
立冬日。
我专注于倒塌,众多的石像
没有完整的迂回
针刺的河流冲破的宽域
蝉翼一样的,轻薄
神在倒装
他的瞳孔是木制的条纹
晶状体
那悬于他手中的瓶中的余温在
缓缓松绑
我对星空束手无策。
不要问我还要走多远
要做些什么
夜晚执行着铁一样的法则
那是一种宗教式的神秘
和冰冷
宛如初生的小婴儿般
无知无能
我对星空束手无策
椅子上的洞(组诗)
椅子上有个洞。
玛瑞娜将会在某个时刻
使用它
或一直不
最终他们合力搬开了
之间的方桌
那是一种向下的松绑
或解除
如移开一座扼住风口的
山峰
椅子上的洞。
我将它称之为玛瑞娜的
洞
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玛瑞娜曾
或正使用这个洞
难以确认
玛瑞娜是否使用过的
这只
长在身上的洞
独一无二的洞。
这个椅子上的洞
绝无仅有
除了玛瑞娜
在长有巨大而
平庸的博物馆
穹顶之下
玛瑞娜悄无
声息地
掩住了这个洞
如往常张开时那样
辐射。
超出树荫构建的范围
我暴露在了白光下面
椅子上的洞依然挥之不去
或应将它称之为玛瑞娜
的洞
“有些孔洞是深渊!”
我可以,铤而走险
或是撤后
与狂燥的蚁群和落叶为伍
嘘声。
有人唤她做
巴比伦婊子
传单上印着这些
有限的比喻
脑中的光幕仿佛
有一颗
黑暗聚拢出的
心脏
椅子上的洞无法
左右这件事
无法印证
玛瑞娜的洞
也不能
人类会复刻所有
既定存在的
行为,除了
此刻意识的瞬时
波动
母体。
玛瑞娜注视我
如同注视所有人
任何人
每一个人
每一只,更迭的物种
玛瑞娜造出
她的洞
如同炮制世间
每一副骨架
每一次冲突、抽打
每一张弓
~
简介:外星人,生于七十年代末,居长江之南。
手机:13636671917
微信:181595884
分享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