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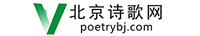

诗人的痛苦
yangyuan 2023-08-04 16:32:29
次品的月亮
吝啬的时辰穿过贫穷的街道,
手里没有更多的富余的灯光,打款;
累了的黄昏穿过群山下了班,它停下操作
那把呼呼旋转的铣刀,风,
无须加工那些快要完成的订单。
次品没有光芒的月亮,
泡在生锈的水塘。
接班的夜晚把它捞出,晾在几片树林
交叉搭建的支架上。
用巨型的游标卡尺量一量,
测下用思念将它浇铸的每片风景
在岁月中滋长的刻度,
间隔了多少的民居,城镇,乡村,省份。
在这座敞开的厂房,
我瞧了瞧废品筐,从流浪的身体上,
取出藏匿河边的柳树,蛙鸣,
企图打磨晾着的月亮,直到再次它发亮。
用打标机打码,贴上出厂的合格证。
在特定的日期,有游荡街头的人认购这枚月亮,
把它当作胸针别在用愁云做成的大衣上。
诗人的痛苦
如果对诗有一种品质上稳定的追求,
作为诗人的痛苦,我没有写出
自己每个季节中的语言。
诗的喉咙像调零的大地结了冰,
濒临倍受打击的冬天,受困于
一种时代的气候。
栖居在大地上的那些如生物隐藏身形的歌手
藏身保护的洞穴,不再从肺腑发声。
他们等着温暖再次唤醒内心的良知,
迎着那时万物的复苏,歌唱
下一个崭新的世界。
面对着那些像如此的歌手,呱呱的青蛙
伏在夜晚的水田,蛇爬行草丛的嗖嗖,
老鼠的窸窣,或者知了没完没了的知了。
我该用尘世怎样的风度探测这个世界的美学深度?
或者它本就是这样面目丑陋,
美只是来自于诗人的噫想。
追随视线飞越那片拦截树林的每枝每叶,
捕捉掩盖的背后,有一只恐怖的蜥蜴张嘴,
像政客发出要进食的低吼。
企图取代所有生命发出的声调,
摘取一个个虚假的正能量的词汇
编织成花环,戴在尘世细长的脖子:
那些在尘世受苦的身体上,他人的脑壳长着,
代替说话,伺养学舌的鹦鹉也许能理解。
我永不会忘记,我受过的苦,
我领受着,我将受的苦,我厌烦西方,也厌恶东方,
想想世界将下,或已下过的渗着血的黑雨,
无论那一场,或先或后,
而那些可怜的拯救者
的英雄故事引起了我肠胃不适,
并不耽误我在时间的泥泞跋涉。
2022
市场上的人情
相信市场上那些购买者精巧的手,
眼神,像媒婆,带着少许彩礼
来相亲,忽视撮箕上
悬停的难受:层层剥离的包菜裸露
可以做菜肴的鲜嫩,反复检验母亲的种值。
在细雨之中,她披着自做的薄膜蓑衣,
戴着蓑帽,用耙子刚给菜蛙松土。
拿着舀勺在两个手臂上下平衡运动,
像工地上启动的吊机,左右摇摆,
从两个粪桶死死抓住,一天的心血。
即将舀出,不敢磕碰浪费,浇上每蔸……
就这样,她劳作,对菜地比对她儿子还亲,
常常忘记吃饭,在阳光的扶助下,
贫穷的土地变肥沃,长出了包菜,
捆绑在稻叶下,挣脱时间的手掌,结出丰硕。
按季节进入这分工的市场筛选,
等着顾客相中。母亲总是那样诚实,
越过称杆上打探的所有起伏,
不缺少斤两,她从讨价还价中
挣得几块钱怜悯,积攒起一家七口的生活。
她有时不认可,所有聪明给世界造成的痛苦,
尽管取自知识赋予智慧的大脑。
拜访
词语脱落,从解说者的嘴
在飞驰的路上一路述写故事,追着黄昏
绕过那片枯燥没有舌头的树木,
停顿在这栋可供观赏的居所前。
那打开的院门张开双手,
像个酒店迎客的礼仪,拉扯着几盏灯光,
张嘴“欢迎光临”。不要奇怪这样的招待,
在缓缓降临的夜色下,有星空可以凝望
闪烁的群星。在大地上展开
梦,心里投机,此处或远方有一座天堂。
而穿过所有掩盖故事的前门,穿过甬道所有纠结的昏暗,
那些窗台上的盘景,设置的紫罗兰的障碍,
活着的人,该怎样蓬头垢面,在爬行的沟渠——
他的居所找到这些价值:
吃饭,拉屎撒尿,刷牙,睡觉,亲吻,喝酒,
抽烟,打牌;天冷,穿秋衣秋裤,开空调……
当迟来的你,此刻缓缓进入了清醒的后院,
在一道光下晾晒发霉的自身。
2022-9
在天空中的校园
没有假期了,游乐与散心收敛,
久违的校门打开,欢迎学生,也欢迎老师。
在天空中的校园,迟迟而来的雨终于上班。
领取微薄的报酬,街道上一片蔫巴的绿树,
草地上一枝枝枯萎的菊花,雨动了心。
你知道吗?在没有因材施教的世界,
所有事物痛苦承受,阳光的暴虐变态。
在那片灰蒙蒙的墙下的讲台,
他生怕有人拖后退,一手狠抓
不求蜕变的臭水沟的蛆虫,逼着在沤烂物
摊开的化学作业本上交出几只苍蝇。
这样局面,雨躲在群山一通长哭,
止住那些漫长的云里雾里,态度明朗,
展开别样教学,验证入学者的资历。
延迟而来的农人,在铺开的田地上,
拿着锄头急速作答试卷,
种上包菜,土豆,芹菜……
这么多奇葩,这么多古怪,在天空中的校园,
对于渴望不同知识的众生,
不希望阳光或雨水执太久的教鞭,
他们上课几天,休息,备好课后,
最好刮起一阵清爽的风,
拂拂那些失败的心灵堆积的尘埃,找到方向。
这些声音我没写出
白天欢迎清醒的人,就像夜晚欢迎
失眠的人。我失眠随着明月
打开的灯光,来到这里踩着诗行踱步,
那些可仰望的群山,
如此真实,在起伏的风中,
不欢迎踱步的忧郁,向我展示挺拔的坚毅。
派出一只多嘴的鸟打扰,似在无声责备。
鸟的责备落在我的诗句,
我反倒有种清醒,拂过那些山的风,
有不同的方向,吹拂我如木头裂开的脸,
就像削下了一层薄薄的木屑,
扬起刨子,用散发清香的纹理
宣告一种美的到来。我缺少对美的预见,
更多喜欢耍耍嘴皮,制造鹦鹉学舌,
对大地声音之源的污染。
我握锄头的手没有打铁的铿锵,
我打铁的铿锵没有握锄头的耐力。
围着铁桩转与耕种土地 有多大不同?
抖动的双肩告诉我,群山的坚毅。
面对眼前的土地,漆黑起伏的城市,
月亮用同样的灯光照亮
那些流浪无家可归的失眠人:
一个躲避着卖身的女人的脸拥有女人的温柔,
她双手轻柔的抚摸潜入我诗行的内部,
就像我在工厂,听着螺丝,卡座落地,
听着刨床切削铁块的嘶鸣。
拾起的手,操作的手,抚摸的手
与提笔的手相同。我没有写出这些声音,
而月亮带给我多余的激情,
嘲笑我有时企图要做个捉刀吏,
像辆熄火的车,停止强劲的发动机,
等着食槽上它的主人添加奖赏,
然后提着钥匙驾驶。我不需要开启,
最基本的约束已经将我点火,
还有许多路程,轮不到报废。
我将发出我的这些声音,真实而非虚无,
不来自虚构的故事,激情的轮番演说,
对头脑进行数次刷洗;我将发出我的这些声音,
响亮而温柔,就像受挤压的大地
保持一惯的风度,从撕开的裂缝中
喷出内部滚烫的熔岩。
不戴有色眼镜的阳光
地平线上,不戴有色眼镜的阳光
一直在蓝天领路,越过许多树木的障碍,
不理会松树,柏树各自贞洁的思想。
翻过一片竹林的传说,不拷打法海。
也不再去探索喀斯特地貌上
那些楚越蛮夷有过的遭遇;一切的故事,
紧跟光线潦草地打开一张世界地图,穿越所有的
大海,大洲,再翻越一张中国地图,
穿过那些平原,丘陵,城市,落在一张
郴州宜章平和行政图的群山,
将我领到这个神圣而无名的村子:阿嘎姑。
它是地平线上省略的一个点,
没有标注,一条路上可有可无的风景。
对于路过的乡镇干部而言,他也许还能
叫出那个乡上这个死了多年小组的名字,
可是对于我而言,却是我的宗教与朝拜地。
虽说这里生长的人就像新生的弃婴,
他的啼哭从没将世界吸引,但对一个渐渐长大
的婴儿和他父母而言,各有其中隐秘的苦乐。
逼着一个浪迹天涯的人,夜晚,
对着明月,如此追问他的失衡。
2022
不能理解的画作
没有边框,天空的尽头,谁把火烧云
泼在群山的轮廓上,
企图把那些山中的袅袅烟火覆盖,
串上密密麻麻的杉树,松树与众多
叫不出名的树,落地把村庄挤占。
几只有闲心的鸟,时起时落,
在火烧云与众树之间,排解一天的苦闷。
戏弄着就要落下的夕阳。
等待产生好奇,我观看这样的创作,
拽着手上要归家的黄牛,
黄牛不知情,直接拖着
我走向画中。我急着摆脱
这不能解释因果的缰绳,反被缰绳困扰。
而观看这幅画作的人,还有谁,
在消逝的时间中,不得而知。
他是否会像我一样,一时驻足留恋,
没弄清,就不得不走进这幅画,
而他身后,还有谁?我是在读,还是在画?
2022
关注灵魂的导航仪
光线昏暗,带着积聚的乌云拦截。
所有的指路牌都那么明确无误,
在即将到来的夜色中引导方向盘。
保证助燃你生命有限行程的油箱
缓慢消耗,能途中进入加油站
再加几升爱,继续的前行中
在你身体轰响的内燃机不能完全消解,
那些掺杂的沉重,
仍会隐秘地排出飘散的恨,
污染空气,袭击路旁偶尔经过
像树木似的行人的肺。
命运总是偷偷造就这些伤感的事物
制造恐慌。伴着轰响的雷声
已甩出交叉的雷电。告诉暴雨
即将或已经在夜色中降临。
警示远远打开的车灯,关注灵魂
的导航仪,避免突发事件。
你一路驾车迎着所有的雨,
穿越这条盘山公路,
在那支撑整个痛苦童年的山脉中蜿蜒。
当安全离开这个不寻常的夜晚,
你得到迟来的安宁,可欣赏的景观。
2022
一个逃兵的自我简介
遗忘荣誉,掌声,稀里糊涂生活;
无须奋斗,经典上早有我的大名自动加冕。
但这副肉体在尘世有它自身的光荣:
像棵不嫌弃土质随处生长的杨树长大,
被人砍伐,做房梁,木箱,家具,
放入灶中烧成灰烬;或者干脆被驱逐族谱,
做只叉角的羊,被宰杀,
落入他人碗,肥他人肚肠。
都值得赞美,从那些沾满油渍享用的嘴
飞出这两个封神的字“有用”。
把我烂泥巴的一生,扶上了可以装饰的墙,
砌在世界这所精神病医院。
那些先后住着的人呵!瞧见,抚摸
你屋里屋外的一切,有时听见异样的咩咩叫,
可否记起这个现代的名字,杨园。
在他如同游子无可无依靠的糟糕剧情上,
肉体在东方,鬼魂在西方,东方,南方,
北方之间飘荡。他也曾在大地上真诚活过,
甘做一个患世界病的病人,
而他早已从“那些可笑的亲人”
发动的事事要赢的战争中,逃脱,
不愿成为炮灰,做个逃兵,一切不治而愈。
2022-10
分享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